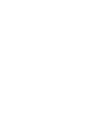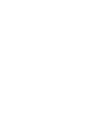让你合成药剂,你合成九转金丹 - 第205章 灶王爷下岗,我来顶班
那一嗓子闷响过后,地面像是被人狠狠踩了一脚的席梦思,晃悠了两下就没了动静。
凌晨三点,街道空得只剩风颳过塑胶袋的沙沙声。
凌天蹲在那堆已经被烧得变形的“移动烧烤车”残骸旁边,嘴里叼著根没点著的烟,手里正跟一堆皱巴巴的零钱较劲。
他把一张沾著油渍和孜然粉的十块钱在膝盖上使劲蹭平,借著路灯那点惨白的光,对著防偽水印照了照,確认没假,这才小心翼翼地塞进兜里。
地上那圈原本耀眼的火光已经熄了,只留下一道道暗红色的纹路,像乾涸开裂的河床,偶尔还在砖缝里闪过一丝微弱的金光。
旁边地上还散落著几张红彤彤的百元大钞,那是刚才几个开跑车的富二代扔下的,说是看著热闹,赏他的。
凌天连看都没看一眼。
他伸手把那个被熏得漆黑的铝锅拎过来,锅底还沾著没化开的猪油。
他把兜里刚整理好的、一共三百二十块钱的零钱,一股脑全塞进了锅里。
“钱这东西,脏点好。”
凌天屈起手指,在锅底“噹噹”敲了两下,声音清脆,像是某种信號。
“听好了,今晚这火是用这些零碎钱买来的。这叫等价交换,也是『烟火气』的规矩。要是拿了那帮少爷小姐施捨的大钞,这火就变味了,成了乞討,那天上的东西能把你这一锅连锅端了。”
铝锅像是听懂了,锅身微微震了一下,把那几张皱巴巴的纸幣“吞”了进去——不是燃烧,而是直接没入了锅底的金属里,化作了一圈细密的铜钱纹路。
凌天拍了拍手上的灰,站起身伸了个懒腰,骨节爆响。
“我也不是什么大善人,灶王爷下岗了,总得有个临时工顶上。不过这活儿不好干,得有人信才行。”
与此同时,七公里外的疾控中心停尸房。
这里的冷气开得比平时低了五度,冻得人骨头缝里都发酸。
苏沐雪手里捧著那本家族秘传的《守陵录》,书页被翻得哗哗作响。
那一排不锈钢冷柜上,数据终端正疯狂跳动著红色的乱码。
她把那一具具尸体的领口扒开,盯著那些尸斑下浮现出的金色纹路,又低头看了看书上的插图。
那是“地脉共鸣图”。
“疯子……”苏沐雪的手指有些颤抖,指尖划过书页上泛黄的文字,“这根本不是病毒变异,这是上古的『万民愿力碑』铭文简化版。”
她猛地合上书,呼吸急促。
凌天那口看起来隨时会漏汤的破铝锅,根本不是什么做饭的傢伙事,那是整个阵法的“阵眼”。
他不是在烧烤,他是在用那些凡人的情绪做引线,强行给这座城市休眠的龙脉做心肺復甦。
那些吃了肉串、讲了故事的人,就是活著的祭品——不,是活著的节点。
苏沐雪咬了咬牙,掏出加密手机,直接拨通了市考古局值班室的內线电话。
“我是特別行动组苏沐雪。老城区地下热源异常,初步判断是古河道地热上涌,可能有文物出土跡象。申请立刻封锁周边地下管网,任何人不得擅自勘探。”
掛断电话,她看著冷柜里那些逐渐安详的尸体,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
以前她的任务是替组织把这些“异常”擦乾净,现在,她要帮那个酒鬼,製造一场谁也挑不出毛病的“合法异常”。
地下管网深处,霉味和铁锈味混杂在一起。
洛璃盘腿坐在二十四台录音机的正中央,这里的空气潮湿得能拧出水来,她的头髮湿漉漉地贴在脸颊上。
她戴著耳机,那里面循环播放著几千条剪辑过的音频。
“妈,我回来了。”
“今天的红烧肉真香。”
“別怕,有我在。”
这些细碎的、毫无逻辑的日常短语,被她剪切成三秒以內的片段,混入了老式收音机特有的“沙沙”白噪音里。
她熟练地推起混音台上的推桿,將这些信號通过改装过的地下通讯电缆,全天候、无差別地向地面广播。
这种频率人耳听不见,但大脑皮层能接收到。
显示屏上,代表“静默侵蚀”的那团黑色阴影,在这些白噪音的衝击下,渗透速率直线下降了67%。
洛璃摘下耳机,从那个廉价的蛇皮袋里摸出一罐啤酒,“啪”地拉开拉环。
她举起啤酒,对著空荡荡、黑漆漆的隧道敬了一下。
“敬你们,这操蛋但没剧本的人生。”
第二天,天刚蒙蒙亮,早市喧闹的人声就把昨夜的死寂冲刷得乾乾净净。
凌天推著那辆经过连夜“爆改”的烧烤车,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了菜市场的入口。
车头上掛著块刚写好的木牌,字跡潦草得像鸡爪子刨的:【本店供奉“人间烟火神”,香火钱十元起,概不赊帐】。
几个早起买菜的大爷大妈围著指指点点,都说这小伙子想钱想疯了,或者是哪个精神病院跑出来的。
直到一个提著菜篮子的中年妇女,试探著扫码付了十块钱。
她刚转身走了没两步,兜里的电话就响了。
电话那是她那个自闭了三年、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的儿子打来的。
“妈,饭好了没?我饿了。”
那妇女手里的菜篮子“啪嗒”一声掉在地上,西红柿滚了一地,她却捂著嘴,在人来人往的市场口哭得站不直腰。
这消息就像长了翅膀,不到半小时就传遍了整个早市。
陆陆续续有人跑回家,把家里那些用了几十年的旧锅、缺了口的破碗,甚至是被油烟燻得发黑的菜谱都抱了过来,要给这“烟火神”上供。
“我不收破烂。”凌天翘著二腿坐在车斗上,手里盘著两个核桃——仔细看那是两个被烤乾的牛腰子,“想供奉,讲个事儿。讲一件你自己都捨不得忘的事儿。”
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头讲了他年轻时为了省粮票,把馒头留给媳妇,自己喝了三天米汤的事。
一个纹著花臂的大汉讲了他第一次给女儿扎辫子,手抖得像帕金森的事。
每说完一个故事,凌天身前那个炉子里的火苗就猛地往上一窜,顏色也从普通的橘红,慢慢变成了一种温润的青金色。
深夜,月亮再次掛上树梢,那道横贯月面的裂缝显得更加狰狞。
凌天避开了所有人,把白天收集来的那些充满了“人气”的旧物,统统倒进了农贸市场中心的一个深坑里。
他往坑里倒了一桶掺了六十五度二锅头的泥浆,然后从贴身的口袋里,摸出一截黑乎乎的木头。
那是乌木,更是他当年自封法力时,亲手削下来的一片指甲所化。
他把这截乌木插在泥浆正中央,既没念咒,也没掐诀,只是极其粗鲁地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。
“老子这辈子不信天,也不拜神。”
凌天拍了拍手上的土,声音低沉,却像钉子一样扎进地里:“但从今往后,这城里每一口热饭,都算我凌天烧的。谁想掀桌子,先问问这地底下的火答不答应。”
话音刚落,整个农贸市场的地面微微一颤。
一股肉眼看不见的暖流,以这截乌木为圆心,顺著地下的排水管、燃气管、甚至是老鼠洞,缓缓向著整个城区扩散。
而在遥远的高空之上,月背深处的那道裂缝边缘,几滴暗红色的液体缓缓渗出,滴落在虚空之中,宛如神灵流下的血泪。
就在这时,远处的街角传来一阵低沉的引擎轰鸣声。
三辆刷著蓝白漆、顶灯还没亮起来的麵包车,像幽灵一样无声地滑过了路口。
车门上印著一行反光的大字——“城市综合管理行政执法局”。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